突破3%的红线!中央发行国债1万亿,有何影响?
国家终于发债了,10月24日,中央财政增发国债1万亿,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信号,财政赤字率突破3%的红线,提高到3.8%。当前全球经济前景不明,中国经济虽然完成全年5%的增长目标不是问题,但是依然存在不少困难,美国保持高息长达一年多,中国货币政策继续宽松的空间有限,所以要从财政政策发力,此前受限于财政赤字率的约束,在国债上一直不敢有大动作,这次增发1万亿国债是一个非凡的迹象。

1、有利于灾后重建
这次增发的1万亿国债的目的在于支持灾后重建,并且提升防灾减灾救灾的能力,近年来,我们国家多地遭遇暴雨、洪涝、台风、地震等灾害,部分地区受灾严重、损失重大。
以2023年前三季度为例,各类自然灾害造成近9000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,因灾死亡失踪499人,倒塌房屋11.8万间,严重损害42.2万间,一般损害103万间,农作物受灾面积超过9700万亩,直接经济损失就高达3083亿元。
这就涉及到两个问题,第一是灾后的恢复和重建,第二是提升防灾减灾救灾的能力。
而这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,而当前的地方政府显然是压力比较大的,三年疫情,地方财政支出增加,而税收收入减少,同时房地产行业下滑,土地出让金也大幅萎缩,这都让地方财政感觉吃不消了。
当前财政发力要找到切入口,而灾后重建无疑是目前最合适的一个地方,一方面,全国自然灾害严重,灾后重建刻不容缓,而地方政府显然目前已经财政十分吃紧,而中央财政通过国债的方式筹集资金, 并且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下发到地方,本息都是中央支付,地方政府没有了财政压力,债务结构得到了优化。
同时,这也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增长,灾后重建必然产生GDP,生产生活恢复后必定能够带来更多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量,这是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方式。

2、调节经济增长方式思维发生变化
本次中央财政增发国债的意义还不仅于此,更重要的是调节经济增长方式的思维发生了变化,调节经济增长的方式一般有三种,货币政策、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,货币政策是我们常见的,主要由央行负责,主要是针对利率升降以及货币松紧,近年以来货币政策一直是相对宽松的,降准和降息也已经实施了多次,这考虑的主要是融资成本。
产业政策是更加具体的,比如光伏产业、新能源汽车产业以及半导体产业,这三大产业我们国家都是有非常明确的产业政策来指导发展的,目前来看,光伏产业已经是全球第一,技术领先性全球第一,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也是全球第一。而新能源汽车产业目前也如火如荼,动力电池全球第一,终端品牌也是多企业齐头并进,比亚迪的销量更是全球第一。至于半导体产业目前华为手机凤凰涅槃就能说明问题了,中国将建立美西方国家之外的第二套产业体系。

而财政政策方面一直比较谨慎,因为财政政策意味着政府要多花钱、多支出,势必会造成赤字率提升以及债务增加,我们国家从新中国以来对此都是比较谨慎的,始终认为这是寅吃卯粮的做法。
但是实践证明,在经济低迷甚至衰退的时候,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、增加政府杠杆是有必要的,凯恩斯经济学已经说明了这一点,而上世纪30年代美国的经济危机最终也是在美国总统罗斯福新政下走出来的。
罗斯福新政核心的一条就是政府要多花钱,要多建设公共工程,还要“以工代赈”,这种解决危机的思路其实在我们国家古代已有之,只是那个时候没有现代国家的财政体系,更是没有发债制度和体系,政府无法通过举债放大财政政策的效果。

3、适当放大中央财政赤字率是有必要的
我们常说经济增长有三驾马车,投资、出口和消费,当前出口下滑,消费稍好,投资一般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,经济就是投资、生产、储蓄和消费,而政府既有生产能力又有消费能力,尤其是中国的政府,有庞大的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,在个人以及民企没有能力或者意愿消费和生产的时候,那么政府就得站出来扩大投资、生产和消费,政府这个时候就不能在拘泥于自己多储蓄。
这是一种逆周期调节方式,现在很多企业没有订单,业务下滑,企业的投资意愿必然下滑,那么企业的投资也会下滑,这会进一步导致就业岗位供给减少,那么就业市场就会面临薪水下降甚至是裁员的现象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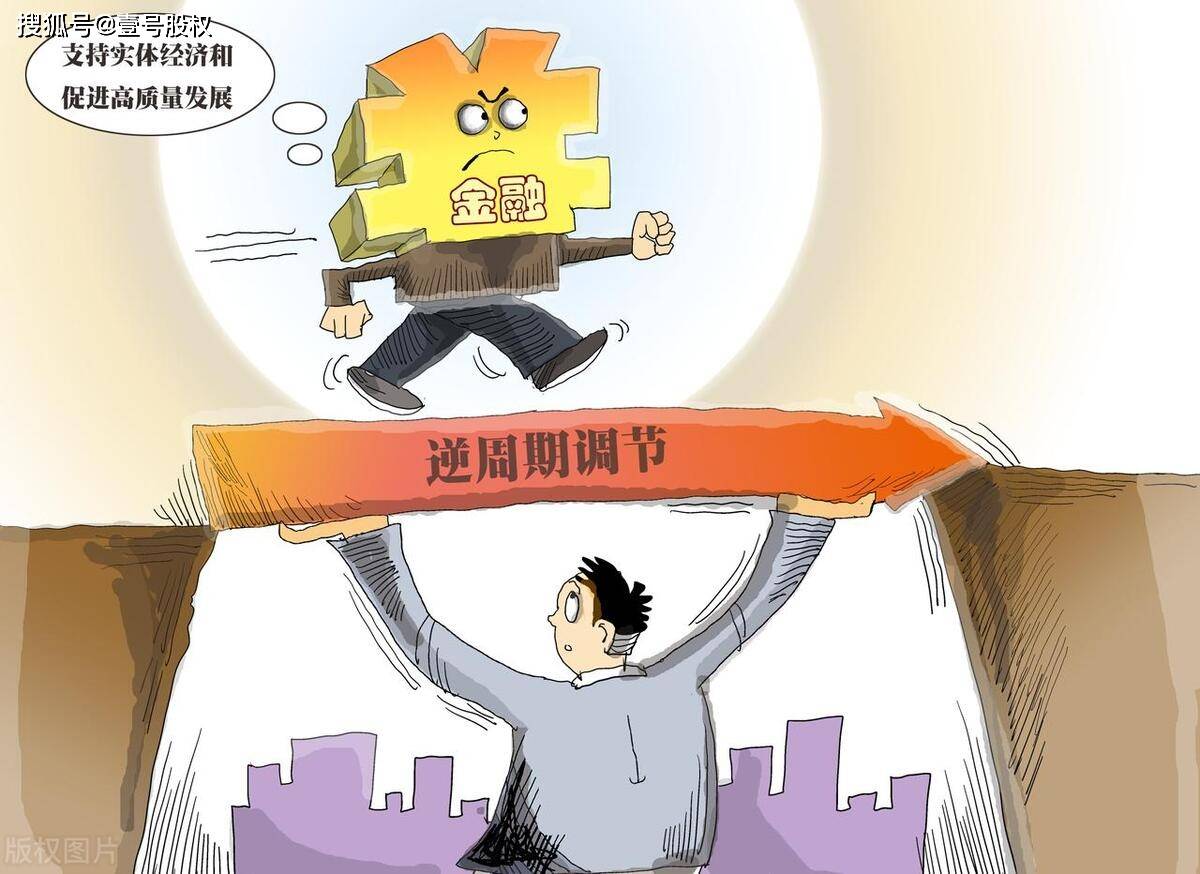
政府需要站出来,担当起责任,主动扩大投资、生产和消费,让民企能够跟在后面能够拿到订单,让就业市场的工作岗位多起来,老百姓有了工作,拿到了工资 ,自然会去消费,这会刺激消费市场的复苏,民企也会进一步受益,等到投资市场以及消费市场恢复的时候,政府再逐步退出,让民企来承担投资、生产的重任。
中国的政府又分为两级,一个是地方政府,一个是中央政府,地方政府当前的债务压力较大,一方面是债务存量较大,另一方面是债务的利率较高。而中央政府的负债率比较低,而且中央政府的信用极好,利率也低得多。
这个时候政府要增加负债,放大杠杆,地方政府是很难有能力去做的,而中央政府明显是可以的,中央政府可以以更低的利率发债融资,大幅降低债务成本,同时中央政府的杠杆空间还比较大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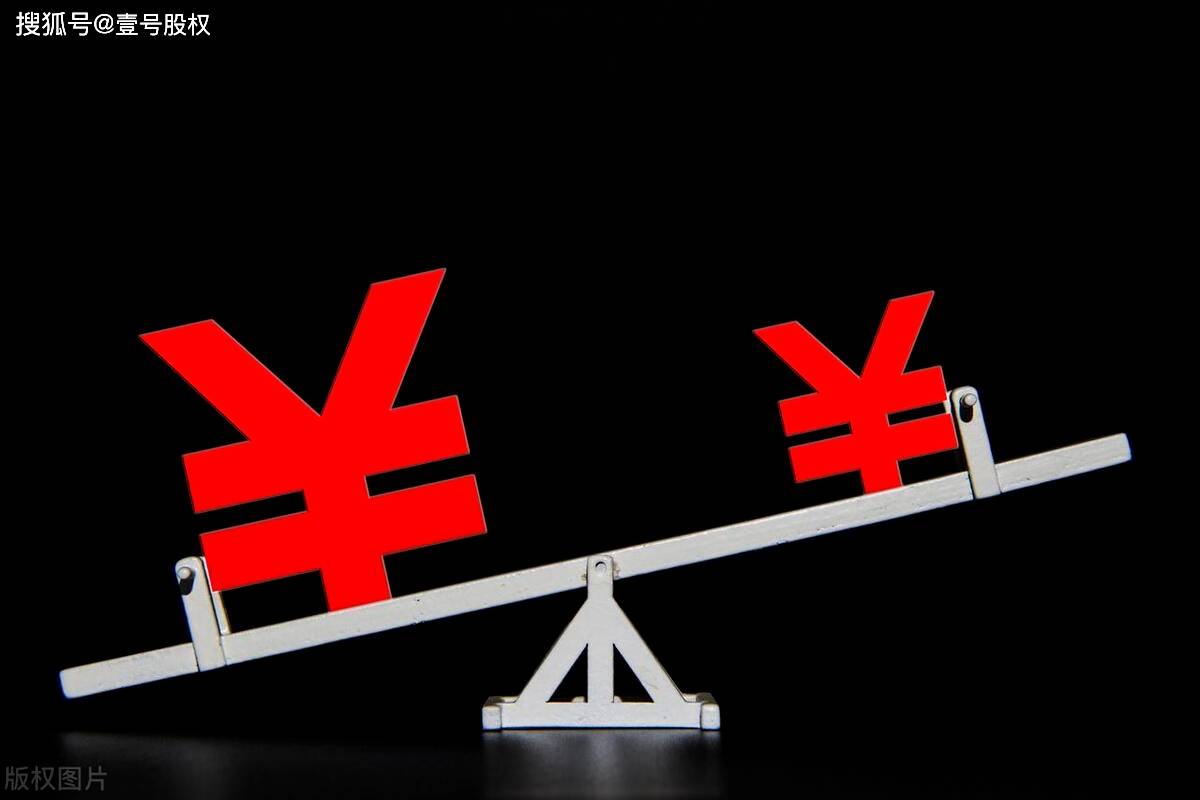
4、中国已有成功经验
虽说新中国以来中国对待债务是偏谨慎的态度,但是在改革开放以来还是更加客观地看待这个事物,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企业,都是需要一定杠杆的,关键是控制好杠杆力度,在不同时期可以有不同的伸缩,那么政府什么时候应该加杠杆呢?
政府的财政作用主要体现在逆周期调节,当整个经济大环境往下走的时候,作为个人和企业肯定是会压缩投资和消费的,这是人性决定的,如果这个时候政府也压缩投资和消费,那么结果将是灾难性的,政府应该扩大投资和消费,为市场提供订单和就业机会,政府应当担负起拉动经济发展的引擎,等到经济复苏,个人和企业恢复了信心,继续消费和投资的时候,政府才可以逐渐收缩投资,让位于市场。
1997年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,整个亚洲都遭受重挫,尤其是东南亚地区,外资大量撤离,货币贬值,失业率暴涨,资产价格暴跌,经济发达的香港都有人因此跳楼。

中国最后是如何渡过难关的?做了几个大动作,1998年实施房改,取消了福利分房制度,商品房成为主流,为房地产投资拉开了序幕。其次是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,在西部实施了大量的投资。第三是开启了基建狂魔的征程,1997年末,中国的高速公路里程不足5000公里,1998年增加了近4000公里,1999年继续增加3000公里,2000年增加了近5000公里,2001年到2010年平均每年新增近6000公里。要知道1997年的时候中国所有的高速公路还不到5000公里,这还是中国几十年的成果。
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,中国推出了4万亿投资计划,比2000年开启的基建计划更为庞大,2011年到2020年的十年时间,平均每年新建的高速公路接近9000公里。2008年中国营业的高铁里程仅仅672公里,2010年增加到5133公里,2015年增加到1.9万公里,2021年达到4万公里。
过去20多年,中国渡过各种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就是要逆周期投资 ,政府敢于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,敢于逆周期投资和支出,那么就需要在财政赤字率以及杠杆上不能过于谨慎。
